
一切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到温州去做调研。说有一个人在温州苍南县鳌江边圈了一块儿地,把这个地方叫做中国第一个农民城,自己画了一张地图到温州去招商。花5万买一块地皮,允许在这块地皮上建一间房子,然后你们家门对面的半条马路要你来修。
我去调查的时候,和各项目已经忽悠了2000多人,调查完了他请我吃饭,我们就在龙港边上喝白酒。他知道我报道出去农民城可能就没有了,他的下场是什么也不好说。喝到一半的时候就突然跟我讲了一句话,说:“吴同志你知道吗?一切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你得支持我。”我当时说你这个违法乱纪分子还跟我讲改革。
但是后来仔细想想,温州人多地少(人均只有两分地)、私营企业全国发展最快,中国最早的一批专业市场就是在温州兴起的,他圈的那块地解决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让个体工商户有地方可以做集约化生产。
回去以后我把这个事儿认认真真地写了一遍,把他那句话也写进去了。这个事儿后来还得到了当时副总理的批示,中央派调查组去调查,最后肯定了龙港的经验,变成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城。
互联网另一半是魔鬼,抹不平山川大河
第二件事儿是关于互联网,我刚刚写完《腾讯传》,对互联网有很多新的理解。弗里德曼写了一本《世界是平的》,说这个世界的千山万水都被互联网一刀削平了。
互联网的原教旨主义是让这个世界没有信息的不平等,任何信息都可以无障碍、免费的到达全世界的任何地方。但是这个世界有哪些人、或者哪一种权利能真正把山川大河抹平呢?
我在北京采访过去哪儿的庄辰超,他当时跟我讲:中国的在线旅游行业1万亿的规模,去哪儿到2016年底可以做到1000亿,携程可以做到2000亿,我们两家每年保持50%的增长,看看什么时候能够做到1万亿?
我说如果你们两家占到8000亿,还剩下2000亿给兄弟们分口粥吃,世界会怎样呢?一定会出现三件事情:
第一,一定会有一户人家控制这个行业的定价权,他掌握了所有的信息。
第二,全中国很多的票务公司、旅行社会倒闭,造成一些人的失业。
第三,那么你这家公司注册在哪里?北京、上海还是深圳?你能统治80%的在线旅游市场,那么就是你一个城市或是一个地方的税务局,会统治这个行业几乎所有的税收。
那么你还能说世界是平的吗?
20多年来,互联网以革命者的名义改变了我们很多东西。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暴露出了它垄断的一面、拒绝开放的一面,以及攫取利润的一面。
这世界上有两种市场经济
2010年的时候,我写了一本书《吴敬琏传》,那个时候吴敬琏老师80多岁。我问他你从一九五几年大学毕业研究中国经济到今天,你对中国改革是怎么看?
他说1978年改革开放,那时候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手脚被绑住的巨人。你只要拼命把这个绳子解开来,手脚能够舒展开就可以了。所以所有的变化都是对的。
到了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这批经济学家的自信心到达了顶点。1998年中国搞了一次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造,在此以后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起来了、中国的外贸行业起来了、中国的产业转型三年间完成了(这个要感谢朱镕基)。2000年中国也加入WTO了。
中国从1978年到2000年,花了20多年的时间,终于把这个巨人的绳子都解开来了,现在还全球化了。中国的商业法律即将跟国际全部接轨。中国的改革会自动实现。
我最近在写企业史。现在是2017年,中国的改革自动实现了吗?为什么那么多企业家移民?移民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在2009年。
到今天,我认为中国一切以发展为硬道理、以速度为契机和荣耀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拿着“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理念去经商,他是会被抓起来的,而且赚不到钱。
所以,到今天我对变化有了新的理解,我认为变化是有好有坏的。我写完《吴敬琏传》以后,请吴老师写一个题记,吴老师写到——“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这个词儿是1994年出现的,到了2010年的时候吴老师说要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市场经济:
第一种市场经济:好的市场经济。
第二种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
首先,我们要摒弃坏的市场经济。原来说用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就是一次革命,后来发觉没有成功,因为有好的市场经济、有坏的市场经济,有好的互联网、有坏的互联网。所以变化是有好有坏的。
第二,我认为好的变化是不会自动发生的,咱们都是做企业的,今天要转型升级。
我们必须要试错,要有人去付出、牺牲。不管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还是一个阶层,我们都要有好的处境来获得更多的利润,我们要改善企业的面貌,还要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所有的变化我们都要去努力争取。
所以在最后,我们要理性对待变化。
三年前我提到要把世界交给80后,80后特别高兴,但其实远远没有那么简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价值,也没有必要献媚年轻人。
刚才陈泽民陈总讲50岁创业、70岁二次创业,那90后还很牛吗?首先要先活到70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好、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毛病。所以我们面对变化要更理性。
如今的中国“水大鱼大”
我最近在写书,2008-2017年的中国企业史。写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大的焦虑。
我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用两个字来形容过去的30年,叫做激荡。为什么很容易形容呢?因为那就是一个创世记,从0到1跑过来的都是英雄,没跑过来的都是狗熊。现在是从1到N。我怎么来形容2008-2017年的中国呢?
我在参加活动时问过周其仁老师,他想了片刻,给了我一个答案——“水大鱼大”。
近十年,中国经济规模很大,超过了法国、德国、英国、日本……我们的货币总量都大了三倍。水大鱼大,规模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恐惧。水大了以后这里面的鱼就变大了,出现了鲸鱼、鲨鱼,也出现了重大的冲突。
鱼大了,小鱼变成大鱼,鱼本身面临转型升级,鱼和鱼之间(行业之间)出现跨界。今天全世界的十大银行,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花旗银行等,但他们未来的敌人一定不在这个名单上,很可能是那个杭州人(马云)。所以鱼的跨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所以为什么要创变呢?因为你原来的东西都是错的,既得利益就跟沙子一样,你捏得越紧,流得越快。所以必须要面临一个大的变化,我们在这场革命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
企业改革要向死而生
这些年我跑了很多传统企业,有三个关键词跟大家分享:
关键词一:归零
我们每个人要想清楚一件事儿,30年来企业所形成的很多能力,面向未来可能都会变成负资产。因此,要以一种归零的心态做事。
关键词二:不适
做企业每天都要有一种不适感,总觉得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是自己不知道的,或者有人跑得比自己快,或者别人有一种更好的模式。我写《腾讯传》用了八个字“小步迭代、试错快跑”,这是互联网的精神。就是用一种实时应对变化的心态,去面对种种的不确定性。
所谓的灰度管理、生态型组织,其实都是面对不适性的企业的自我应对能力。
关键词三:必死
当我们离开这个会场拥抱创变的时代,我们要告诉自己,变化是会让我们死的。今天中国每年有100万个年轻人创业(97%的死亡率),我们要抱着必死的心去改革。
归零不是必死,我认为是我们这一代人(今天的这些企业家朋友)面对未来的一种姿态。
我并不认为过去10年我过得非常愉快,而且未来10年,中国转型的速度会比我们想象得还要慢一点。但是,我们是企业家,我们是要自己负责任的人。
最后用尼采的一句话结束今天的分享——无论这个时代怎样,我们必须在自己的身上克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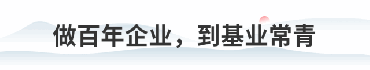






















 星巴克
星巴克 中兴
中兴 摩拜单车
摩拜单车 海底捞
海底捞 凡客诚品
凡客诚品 腾讯
腾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