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全国有30个省市自治区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增幅大约在24%。进入今年以来,目前有6个省再次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今年还会有相当多的省区市要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这是 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对中国去年以来发生的薪酬整体上涨的阐述。
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性提高劳工薪酬,其中既包含着政府对民生的关注,也不乏各地区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对越来越稀缺的人力资源的抢夺。尤其内地各省份、非一线城市对薪酬大刀阔斧的调整,早已连续多年将西部沿海省份和一线城市的平均薪酬增速甩在了身后。加薪正在成为新一轮资源分配调整的起点,在劳动者工资单数字的背后,展现的是区域竞争的博弈力量。
政府介入劳动者薪酬定价领域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希望通过“劳动力成本提升传导压力”来刺激产业升级的愿望。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原材料价格全面上涨,劳动力价格普遍上涨的浪潮亦同时涌现,毋庸讳言,对于沿海发达城市而言,“刘易斯拐点”确实已经来临。
在教科书之中,“刘易斯拐点”论提供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即劳动力要素在无限供应时,由于供过于求而毫无议价能力,而当其供求关系逆转时,其议价权将大幅度提升。但是,与经典的教科书论述中只有城市-农村两个经济部门的模型不同,在中国,我们所见到的经济结构是“国内市场-国外市场”,以及在国内市场中的“城市-农村”两个层次的市场部门。在这一模型中,议价权的争夺战有着更为微妙的力量均衡和更为丰富的层次变化。
必须看到,在农村劳动人口无限供应的漫长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在城市经济部门之外,还存在国外市场因素,这导致中国的沿海城市未必是农村劳动力价格被压低的最大获益者。恰恰相反,由于在国际垂直分工的经济结构中,中国处于所在的低端制造环节往往处于利润微薄、定价权旁落的不利地位,因此,很有可能在漫长的中国的外来工入城过程中,最大的获益者是国际贸易部门和国外的消费者。
有数据显示,1955?2009年,日本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重平均为17.75%,而中国2009年 上市 公司中,所有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重仅为8.9%。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严重低估,即使按照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速20%,至少还可以持续9.29年。
这就带来了一个重要的疑问,即当中国的农村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为供不应求时,劳动力价格向合理回归,中国的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有没有能力大幅度提高劳工的薪酬?要知道,作为定价权掌握者和最大受益者,当中国的劳工成本提升时,国际资本完全可以采取转移的方式,来继续实现劳工价格最低化。这就是说,中国的劳动力供求拐点未必是全球的劳动力供求拐点。
从本专题中的珠三角劳动力收支调研中,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力成本提升带给制造业的压力,正开始向贸易商和品牌厂商传递。如果说,前两年制造企业还在忧虑如何争取贸易商和品牌商的订单,那么现在,则轮到了贸易商和品牌商主动找工厂帮忙生产。长期以来,它们都是整个产业链条中利润最高的环节,当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每个中间商都面临选择,要么利用其品牌影响力说服客户和消费者为增加的成本埋单,将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压力传递到下游、甚至终端消费者,要么它便需要从自己的利润空间中挤压出一部分消化这部分成本。
那么,作为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0%左右的出口大国,中国是否有实力在全球 供应链 条上议价,以此系统性地提升中国贸易的竞争力?而另一方面,如果要实现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企业能力的升级,又应该如何处理薪酬手段所难以触及的问题呢?
作者系《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区域经济研究院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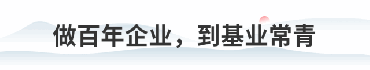























 星巴克
星巴克 中兴
中兴 摩拜单车
摩拜单车 乐视
乐视 海底捞
海底捞 腾讯
腾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