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天下秩序中,“西方”具有特别的意义。“西”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对“西”的认识,也是渐进式的。开始只是指今新疆和中亚地区(如周穆王时代),后来包括了南亚次大陆(如玄奘西行时),更后来包括西亚的波斯、西南亚的阿拉伯以及东罗马帝国,郑和时代又涵括了非洲东海岸。明清时期接触到欧洲人,知其所处地域比历史上所接触之地更靠西,则“西”的概念又扩展为欧西,并呼以“泰西”“远西”,以示与早年之“西”的区别。
近代以来“西”的地理概念淡出,文化内涵加重,并且比较明显地定格为欧美文化。我们讨论的“西方”便随着历史步伐的演进而转移,大致在明朝中期以前指中亚、印度、西亚,略及非洲,晚明前清时期指欧洲。
大航海之前人类重要的文明区域,除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外,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印度教佛教)文化圈、西亚北非(伊斯兰)文化圈和欧洲(基督教)文化圈,都属于“西”的范围;人类最重要的具有源头性的四大文明中,其他三大文明所在的区域都位于中国的西部。在历史上,欧洲文明与西亚、北非及印度文明的亲缘关系十分密切。首先是语言学的联系,共同的印欧语系把遥远的印度和英伦三岛、莱茵河畔连接为一体;其次是宗教的联系,希腊宗教、印度教、波斯古代宗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思维共性或历史联系,为东西方学术界所共同认知;而由此而来的西亚大陆及地中海周边地区拥有共同的神话、知识和难题,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此外,还有战争的纠葛,比如希腊波斯战争等,造就了欧洲文化的综合性。古希腊文化是欧洲文化的源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远征使西亚和北非经历了长期的希腊化时代,
虽然这些地区的居民早有自己的发达文化,希腊文化不能真正取代当地文化,但它们对彼此都留下了很多融合痕迹。神圣罗马帝国的文化不仅继承了雅典和罗马的古典遗产,而且也结合了西亚地区的文化。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就带有强烈的西亚文化精神,以至在许多方面湮没了希腊文化的传统。罗马通过武力征服向欧洲各地传播的正是这样一种综合性文明,在公元1000年前后被及今天的整个欧洲,以至公元600—1100年间,欧洲的古典传统黯然失色。因此有人说欧洲中世纪是东方文化对于罗马的胜利。中世纪后期,希腊文化才在欧洲重新显现,然而又是以阿拉伯文化为中介重新显现。中世纪的拜占庭文化中,西亚特色和希腊化时代的特色更明显。
所有这些,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真正的东方,不在苏伊士,不在高加索地区,而在天山。天山以西的所有文明实体,都具有某种共同的历史、宗教、语言、战争方面的联系,共同映衬出中国文明的独特性。“西”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异域文化。
中国古代有几个词涉及对于世界的看法,比如“四裔”“天下”“绝域”。中国古代的世界观念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仅指“中华”,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第二个层次,包括中华和四裔(夷狄),共同组成中国古代的天下观,这个天下的秩序通过朝贡来维系。该层次的“天下”大体相当于今日的东亚世界。第三个层次包括了“绝域”。绝域一般指遥远的西方世界,不包括东亚各国、各地区。
用现代概念简单地说,中国古代有一个“东亚世界”和“西方世界”的观念,东亚世界都笼罩在中国文化圈之内,是中国人“天下观”的主要内容。在东亚世界里,古代中国的国家政策以追求一种文化上的统治地位为满足。对于东亚世界的成员,只要接受中国礼义文化,就可以被纳为朝贡国,否则就有可能发生冲突。这主要是出于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考量。
对于西方世界(绝域),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异域外邦的意识,“西方”从来都是一种非我族类的外来文化的神秘之地。对于西方人的朝贡,中国皇帝从未做出刻意追求。1500—1800年,西方国家企图以自己的方式挤进东亚秩序,一再遭到拒绝。从宏观层面考察,历史上传统中国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模式,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截至郑和下西洋时代,即15世纪以前,为第一个时段,可称为古典时期;1500—1800年间的三个世纪可以算作第二个时段,一般称为近代早期;鸦片战争前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以算作第三个时段,是近代时期。
这三个时段各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在第一个时段,中国在中西文化交往中始终处于比较主动的、强势的地位。原因是在该时段中国长期在经济、科学和知识等各个领域领先于周边国家。在第三个时段,中国因为落后挨打,处在比较被动的、弱势的地位。只有在第二个时段,即晚明和前清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也就是16至19世纪初,中国与西方基本上处在政治上对等的地位,虽然该时期中国在经济和科学领域已经逐渐落伍,但西方文明的东渐和中国文化的西传却保持互惠和平等的格局。
16至18世纪的中西交往与此前和此后相比都有鲜明特点。12世纪以前的中西交往主要是中国与西亚、中亚、南亚的交往,而中国与欧洲人的直接往来极其罕见,这就不用说了。13、14世纪,欧洲的旅行家、使节、传教士开始设法进入中国,但他们都是通过西亚的陆路前来:进入西亚之后,或者北上俄罗斯大草原抵达中国边境,或者南下波斯湾经过一段海路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而且这些零星来访者在中国多数行色匆匆,元代在北京和泉州曾建立天主教教区,无奈时间不长且在此工作的欧洲人也很少。16世纪末,随着欧洲各国航海事业的发展和海外殖民势力的扩张,欧洲人频频由海路造访中国,大多数绕过好望角斜插印度洋,或经由美洲贯穿太平洋,取道西北陆路者很少,几乎只是俄国人的专利,西欧各国虽多次努力想从俄国借道,但成果微茫。这成为16世纪之前中西交往的一大不同。
在19世纪的中西交往中,欧洲人仍然是以海路前来为主。但与16世纪至18世纪的显著区别在于中西文化交往的媒介。16世纪至18世纪来华者虽不少,但能够承担中西文化交流使命的只以一个群体—耶稣会士—为主。耶稣会士既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观念,也深刻影响了欧洲人对于中国的看法。作为一个整体,耶稣会士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成为该时期欧洲人认识中国的起点,成为欧洲人勾画心目中“中国”的基础。
近代中国社会开始全面卷入以欧美为主导的世界化进程中,而且由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成功西化,西方世界的第二号经济大国居然出现在中国的东方,因此“西”的内涵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意义,完全成为一个意识形态和文化概念。原来那种地理和文化混合的“西”已经不复存在。而印度和西亚北非这种传统世界中的“西”,也变成了非常“东”的世界。东方和西方不仅仅是一种异质文化的概念,还是一种关于先进工业文明与落后农业文明的概念。当欧洲文明愈来愈显现其经济活力和技术进步时,“中”与“西”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追求国家进步,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过程。
这一过程可以从距今三个甲子的庚子年(1840年)开始。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居然在十年前就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国是唯一具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的总发电量已经接近欧盟和美国的总和。尽管工业化还是大而不强,但是,中国毕竟已经昂首行进在工业化、现代化的大道上。于是,中西之间的文化关系也与19世纪晚期以来一百多年的单向流动不同。中西之间的文明交流与互鉴,不仅有了丰厚的传统文化渊源,而且有了不一样的物质和经济基础。中国人如今更需要讲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也更有底气讲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就是这种情况下对于全球化的中国回应。“一带一路”不仅是传统丝路文明在现代的延伸,而且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桥梁和纽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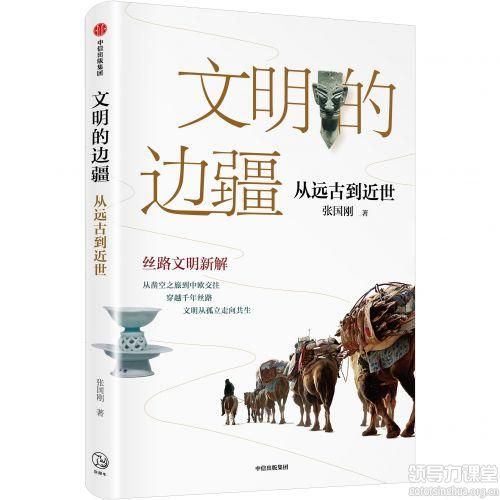
(摘自《文明的边疆》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2月版)

















 加多宝
加多宝 vivo\oppo
vivo\oppo 亚马逊
亚马逊 海尔
海尔 IBM
IBM 美团
美团




